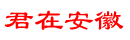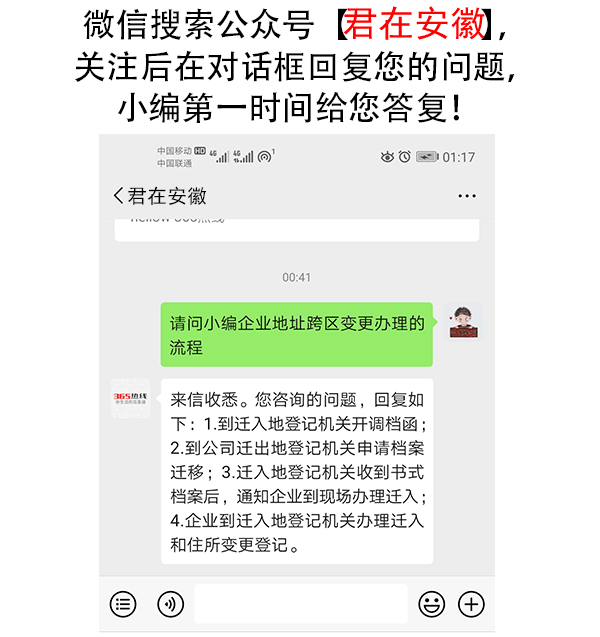2016年恐怕是近年来奥斯卡金像奖最难猜的一年。尤其最佳影片大奖竞争形式混沌,原本在各大影评人协会奖领走的是以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《惊爆焦点》(Spotlight),没想到金球奖却把戏剧类最佳影片给了《神鬼猎人》(The Revenant);结果另一个大指标制片人协会奖,却有点意想不到地把奖颁给《大卖空》(The Big Short),现在变得这几部片个个有希望、片片没把握的局面。
即使如此,距离2月底开奖不到一个月的此时此刻,美国媒体吵得最热的话题,却并非究竟谁会拿奖,竟然反而是奥斯卡是否对黑人演员有所偏见的种族议题。
“白“成一片引发争议
起因在于连续2年,美国影艺学院在4个演员奖的40个名额里,都没有任何一位黑人演员获得提名入围。讽刺的是,影艺学院才刚在一三年换上一位黑人女性主席雪瑞·波恩·艾塞克斯。今年入围名单公布之后,演员奖部分再次“白“成一片,多位黑人大牌巨星纷纷发难,例如威尔·史密斯原本呼声甚高、最后却落了一场空,他与太太洁达·苹姬即同声公开抵制,拒绝出席参加今年的颁奖典礼。尴尬的是,今年的典礼主持人偏偏正好是黑人男星克里斯·洛克,甚至还有人呼吁他应该挂冠求去,以示支持。
这波争议,引发另一种反向声浪的隔空喊话。入围最佳女主角的英国女星夏绿蒂·兰普琳(Charlotte Rampling)则反过来批判,这种抵制似乎也是“对白人的种族主义“,她表示,没有人能确定这真的就有歧视或偏见,有时或许只是单纯地因为今年黑人演员的表现,没有好到值得进入最后决选名单。曾2度获最佳导演奖、地位崇高的克林·伊斯威特(Clint Eastwood)选择妙回:“我试着保持理性,但我不喜欢这样。在影艺学院里有好几千人,会员中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得过奥斯卡。“
至于早就“出柜“、演过《魔戒》系列“甘道夫“一角的资深男星伊恩·麦克连(Ian McKellen)则更高明地反问:“多少直男演员演同志角色得奖?那身为出柜的同志演员演直男角色有机会拿奖吗?“等于拐个弯告诉大家,若要谈“歧视“这样的政治性话题,那就当然不只有种族肤色这个层面而已了。
伊恩.麦克连的回答,点出了问题的本质。在任何行业和环境中,都有弱势族群与偏见的存在,如果说黑人被忽略,那拉丁裔、亚裔的演员呢?女性呢?同志呢?基本上,这是结构性的根本问题。哪些人有资格做影艺学院的会员?当它共六千多名的会员,比例上以白人、男性为绝大多数主导之时,当然集体加总出来的意见,就会倾向这样的观点与结果。
奥斯卡金像奖是大评审团制,6000多人各自投票表述,没有讨论、也没有绝对要求片片皆要审视的严格标准。于是乎长年以来,奥斯卡的评选都是集体主义、保守中庸式的倾向。别说黑人、同志、女性一向是弱势了,票房太低的独立制片很难被看到,人缘不好、知名度不高、没钱公关造势宣传的影片影人们,若想被圈选进入围名单里,几乎只能等待奇迹。若要说真正的公平公正,永远是缘木求鱼。
看看公开出柜之后的伊恩.麦克连、鲁伯特.艾略特等演员,始终还没机会在奥斯卡史上抡元;奥斯卡颁出了87届,至今仍只有凯萨琳·毕格罗(Kathryn Bigelow)一位女性直至一○年才得过第一座最佳导演奖。更不用说那年李安执导的《断背山》在最佳影片奖上大热倒灶败给《冲击效应》,谁说跟它的同志议题没有关系?相形之下,所谓对于黑人演员的偏见高墙,其实相对而言,老早就被推倒了。
就表演论表演才是准则
翻开历史,第一位获奖的黑人演员,早在1940年就已出现。那年海蒂.麦丹尼尔(Hattie McDaniel)凭《乱世佳人》里的管家一角,获得奥斯卡女配角奖,从此打开所有黑人演员的小金人之路。虽然整体比例上仍属少数,但包括琥碧.戈博、摩根.费里曼、小古巴.古丁等演员,之后都纷纷有机会上台拿奖。最厉害的纪录是○二年那一年,不仅丹佐.华盛顿(Denzel Washington)、荷儿.贝瑞(Halle Berry)两位同年得奖,双创男、女主角奖由黑人演员获奖的首例,甚至连终身成就奖都恰巧颁给了资深黑人男星薛尼.鲍迪(Sidney Poitier)。
所以这2年名单中少了黑人演员的名额,我倒宁可认为那只是巧合。或许藉由这个问题被凸显的缘故,以至于促使美国影艺学院决定尽快从改进会员的组成结构着手,主动吸纳增加不同种族背景的会员,以平衡观点上的多元比例。由此看来,也算是一桩美事。但反过来因为这波抗议声浪的波涛汹涌,一周前刚公布的“美国演员工会奖“(Screen Actors Guild Awards),颁出了一大半的黑人演员得主,究竟是实力使然,还是受到议题影响的风向所致?相信也不是大家所乐见的质疑。
让作品归作品,就表演论表演,似乎才是唯一不变的准则。如果有一天,不再有任何人需要以实力之外的因素,去论断奖项的评选结果,那才是这些所谓的偏见或歧视的绘声绘影,真正被消弭殆尽的时刻来临。